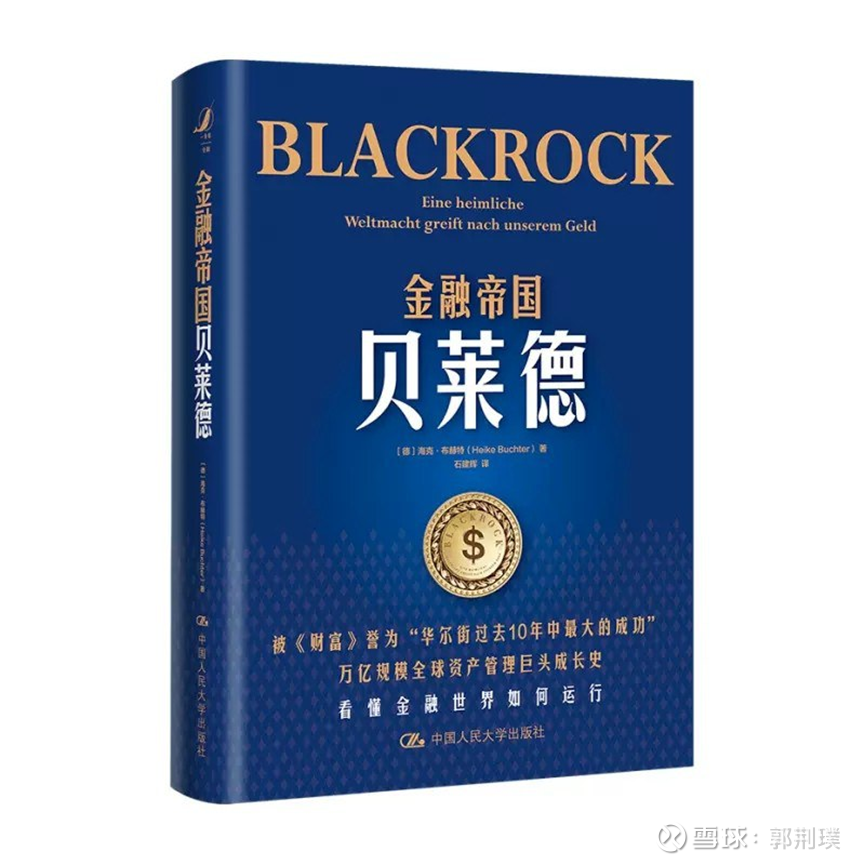(原标题:成功于系统化的执念)
《金融帝国贝莱德》读后感
郭荆璞/文,首发于《证券市场周刊》
按:华尔街的传统风格是傲慢的,高高在上。自2008年以来,华尔街的话语权也在渐渐转移,从高高在上的高盛们手中流逝,而主要的胜利者之一便是贝莱德等超级资产管理机构,甚至有自媒体根据持股名单得出耸人听闻的结论,贝莱德与先锋领航、道富等机构是世界的掌控者,我想熟悉ETF的投资者会对此哭笑不得吧。资产管理机构的崛起给世界提出了新的问题,股东们对这个世界来说,到底承担了什么样的责任呢?从贝莱德身上,我们将会看到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思考这个问题的人们。

声明一下,读书笔记主要针对的是本书的内容,所以有什么偏颇的地方,要怪本书作者,不怪我,哈哈哈哈。

贝莱德(NYSE: BLK)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截至2022年底,贝莱德在全球管理的总资产规模约8.6万亿美元,涵盖股票、固定收益、现金管理、另类投资等各类型资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贝莱德的“传记”,《金融帝国贝莱德》,作者是一位常驻纽约的财经记者,叫海克·布赫特(Heike Buchter),德国人,所以本书有一部分是从德国人的视角开始写的。
贝莱德不仅规模居于领先地位,而且在债券市场、并购、指数基金和被动投资、ESG等方面都走在行业前列。贝莱德时常强调把风险管理放在异乎寻常的优先地位。
贝莱德拥有16,500名员工,在38个国家及地区设有办事机构,为超过100个国家及地区的客户提供服务。贝莱德的客户包括养老金、银行、保险、主权财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以及政府与企业,也服务于个人投资者。贝莱特通过安硕(iShares)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指数基金管理人之一,个人投资者是其非常重要的客户。
贝莱德是许多超大型企业最大的股东之一,这些公司包括从苹果到微软等高科技公司、从GE、埃克森美孚到可口可乐这样的传统巨头,也包括花旗银行这样的金融业同行巨子,还包括欧洲的巨头们,贝莱德曾持股超过4%的欧洲公司有:默克、雀巢、联合利华、欧莱雅、慕尼黑再保险、西门子、SAP、阿迪达斯、巴斯夫、拜耳、科思创、德国邮政等等等等,其中的一些公司,贝莱德都是单一最大股东。
贝莱德曾披露,在1年当中,公司在超过14,000场股东大会上投票。在部分企业的资本结构当中,贝莱德不仅是最大的股东,也是最大的债权人,特别是在一些并购交易当中,贝莱德同时作为并购双方的股东、债权人,和杠杆并购对应的高收益债券的投资人。
毫无疑问,像贝莱德这样的资产管理公司已经在资本市场上拥有了巨大的话语权。《金融帝国贝莱德》的作者在本书开始和结尾都提到了巨型乌贼的意象,贝莱德为代表的资产管理公司的触角,通过资本市场,通过作为股东和债权人的各项权利,触达社会的各个层面和角落,正在重塑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资产管理公司在其中的权利义务和命运,也显得格外引人关注。
2021年10月,贝莱德宣布,公司正在为部分指数基金的机构投资者提供参与代理投票的选择,将赋予部分机构客户在代理投票中的直接发言权。贝莱德已经意识到了它手中巨大的权力,并且努力避免这种权力的反噬。
《新苏黎世报》称赞贝莱德是瑞士市场指数惊涛骇浪中的一堵黑岩(Black Rock),事实上不仅是瑞士市场,全球资本市场的波涛汹涌当中都有这一堵黑岩的身影。《2001太空漫游》当中的黑色巨岩,成为了资本市场上两家最大的管理人的名字,贝莱德和黑石,二者有着久远的渊源,当贝莱德的创始人拉里·芬克(Larry Fink)接受黑石两位老板苏世民(Stephen Schwarzman)和彼得森(Peter Peterson)的邀请,成立合资企业作为黑石公司的固定收益投资平台的时候,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能力,没有想到自己将在短短30年中创立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
2010年,当CNBC采访芬克的时候,记者问他犯过最严重的错误是什么,芬克说,当苏世民和彼得森找到他的时候,“我没有信心建立自己的公司从事风险管理,他们比我自己还要相信我。他们做出了正确的投资决定,我却没有。”
在公司开始的时候,芬克就知道自己要做的事情不是投资,而是风险管理,这个决定是贝莱德走向成功的基石。
一、贝莱德成功的核心是系统化的执念
如果人们面临不透明的投资组合,或者对资产价值存疑,人们就会召唤拉里·芬克的公司。
——《金融帝国贝莱德》,内部人士对完成通用电气剥离基德·皮博迪资产包剥离交易之后贝莱德市场地位的评价
可以说,贝莱德建立在风险管理系统之上,控制风险、管理风险、经营风险,这样的理念是金融机构的入门课,但是把这种理念变成执念牢牢把控,进而内化为一套系统,则是极少数成功者才能够实现的。贝莱德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贝莱德的员工有时候会说,公司“对识别风险近乎偏执”,贝莱德今日地位的建立来自于创始人对风险的执念。
1. 80年代芬克的成功与失败
拉里·芬克最早在金融界闯出名头是因为CMO(collateralized mortgage obligation,抵押担保债券),他在上世纪80年代加入投资银行第一波士顿之后,与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刘易斯·拉涅利(Lewis “Lew” Ranieri)在竞争中共同创造了这种金融创新产品。拉涅利的故事可以参见《说谎者的扑克牌》,他创造发行了最早的私人MBS(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化)。
在MBS的基础上,将基础资产到期时间和风险收益都固定的MBS,打包替换为到期日不同,风险和收益也千差万别的多种抵押贷款,甚至包括风险分类不同,可能是次级贷款等高风险的资产,这就形成了CMO。芬克回忆起80年代向房利美和房地美介绍CMO这种新工具的时候仍然振奋不已,“在我20多岁的时候,我就熟悉这个工具的方方面面以及它如何发挥作用”。
在CMO和CDO(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债务担保凭证,就是把CMO当中的抵押贷款扩大到各类型的基础资产,甚至包括MBS)引发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芬克还曾经对《名利场》杂志表示,至少“当时我们帮助降低了购房成本”。
不过芬克很快就撞上了职业生涯的礁石。1986年3月和4月,美联储两次意外降息,提前还款需求导致CMO大量风险爆发,芬克领导的部门遭遇了流动性危机,损失1亿美元。芬克几乎马上就被第一波士顿扫地出门,尽管他把错误归结于计算机的问题和数据收集不够完善,“非战之罪”。1987年,拉涅利也被所罗门兄弟抛弃。
这两家公司都在不到几年之后遭遇危机。第一波士顿留下”the Burning Bed”的嘲讽(在同名电视电影当中,遭到肉体精神双重虐待的妻子最终选择烧死了家暴男,被陪审团当庭释放),公司在1988年参与丝涟床垫的杠杆并购损失10亿美元,引火烧身而被迫卖身瑞士信贷,甚至在2006年连这个传承近百年的品牌都消失了。所罗门兄弟则是因为违规囤积美国国债,1991年东窗事发时,美国财政部邀请购买过可转换优先股的巴菲特担任临时董事长,试图拯救公司,所罗门兄弟最终难逃委身于保险集团旅行者公司(Travelers,后来与花旗集团合并)的命运。这两家曾经被看作是锐意创新的投资银行,最终都因为无法把握在创新过程中的风险而被迫选择高风险证券或者违规,来保持账面利润的优秀。优秀有时候是优秀者的催命符。
第一波士顿的经历不仅让拉里·芬克获得了华尔街的关注,也凝聚起一支团队。创业时聚集在芬克身边的贝莱德元老,基斯·安德森(Keith Anderson)、芭芭拉·诺维克(Barbara Novick)、贝尼特·戈卢布(Bennett Golub),和罗伯特·卡皮托(Robert Kapito)等人,都是他在第一波士顿期间的死忠粉,安德森和诺维克来自第一波士顿的抵押贷款交易部门,戈卢布是金融工程专家,而卡皮托则是芬克的合伙人和芬克理念在贝莱德的执行者。
2. 系统化对风险进行分析的能力
在第一波士顿经历的大起大落带给芬克的教训是深刻的。错误并不在于损失的1亿美元,这项业务累计为第一波士顿带来的利润远超过损失,但是错误早在赚取利润的时候就已经铸成了。盈亏事实上是同源的。
芬克认为粗糙的计算机程序不能计算当利率发生变化的时候,组合的风险是向什么方向发展的,团队并不清楚利润是如何产生的,也就不了解承担了什么样的风险。“我们不知道为何赚了这么多钱,我们没有必要的工具来了解自己所承担的是何种风险。”第一波士顿时代的利润和风险都是在unknown unknown当中形成的。
在贝莱德建立之始,芬克就决心建立一个系统,能够充分计算由多种到期日、收益和风险各不相同的底层资产组成的投资组合的风险,芬克对组合风险的执念最终化为了贝莱德系统化的能力。
贝莱德的系统初试啼声的交易是通用电气剥离基德·皮博迪资产包,约100亿美元的CMO资产包该如何评估,这个难题阻碍了通用电气出售该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的建议是通过计算机模型计算组合的风险和价值,逐步分拆出售,以获得更好的价格。最终委托成功完成,芬克成为了华尔街应对巨大、复杂、不透明的资产组合时的分析圣手。
由此,贝莱德的系统声名在外,先后帮助FED分析、定价、清算接管了贝尔斯登、AIG和两房的有毒资产包,这些资产(形成了Maiden Lane I(贝尔斯登)、II&III(AIG)三支基金)因为可以不断出售深度折价的有毒部分给央行,事实上获利颇丰。贝莱德还被邀请评估了爱尔兰和希腊银行系统的资产负债表,也参加了英格兰银行对苏格兰皇家银行有毒资产的剥离工作。最终是欧洲央行建立购买私人信用证券的计划,贝莱德作为顾问负责该计划的开发。
在帮助全球央行应对危机的时候,核心的问题是一致的,那就是如何重建信任。危机中最重要的步骤是找到外部专家来证明自己值得信任。贝莱德一次又一次的成功评估经验,既建立起自己的名声,也帮助雇主向市场传递信心——我们已经选择了最靠谱的评估者,请大家把心放回肚子里,耐心等待吧。
有趣的是,几乎每一次,贝莱德给出的评估结果都比太平洋资产管理公司(PIMCO)更乐观。也许这也是贝莱德能够获得评估合同的原因之一。
3. 阿拉丁,全知全在全能
贝莱德的核心数据系统叫阿拉丁。阿拉丁(ALADDIN)有一个拗口的全名:资产、负债和债务以及衍生品投资网络,即Asset, Liability, and Debt, derivative Investment Network,系统的主体位于美国西北部的小镇韦纳奇,这里曾经以“世界苹果之乡”、“美国苹果之都”闻名,清冽的哥伦比亚河水曾经吸引印第安部落内兹佩斯人捕捉鲑鱼,也吸引欧洲殖民者种植小麦和苹果树,今天的哥伦比亚河,则是微软、雅虎、戴尔、T-Mobile等大公司数据中心的电力来源。
贝莱德帮助通用电气剥离皮博迪资产包的时候,所需数据可以储存在一张3.5英寸软盘里面,这张软盘被装裱起来,挂在贝莱德解决方案公司的COO罗伯·戈德斯坦的办公室里,它是戈德斯坦的金唱片。如今阿拉丁系统自动创建180万份报告,同时监测从欧洲利率走势到美国中西部干旱情况等一系列数据,记录纽交所40亿股股票的换手,清算贝莱德的25,000笔交易。阿拉丁由数千名分析师和程序员运行,有规模巨大的服务器和专用线路,有3套备用电源。
阿拉丁提供的能力包括了交易执行、组合管理(对账、清算、业绩归因等)、风险管控、数据管理,和最重要的组合风险分析功能。目前阿拉丁已经被全世界的买方、卖方和监管层采用,甚至包括贝莱德的竞争对手如先锋领航集团。
这套系统主要由操作系统(Aladdin OS)、社区(Aladdin Studio)、可持续发展模块(Aladdin Sustainability)组成,3条产品线以风险控制和归因能力作为共同的核心,借助与Snowflake共同创建的Aladdin Data Cloud,输出能力进行客户侧数据的管理,监控和执行股票、债券、另类投资头寸的交易、清算和业绩归因,计算风险资本覆盖情况,进行压力测试,对ESG状态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评估。阿拉丁系统覆盖了资产管理、组合管理、财富管理等多种类型的客户需求。
通过阿拉丁和贝莱德数百名数据分析师、数千名员工和数以万计的使用者,阿拉丁系统为我们展示了toB软件和SaaS服务的成功模式,那就是真正把使用者的习惯和需求放在第一位考虑。从卡戈卢布和戈德斯坦等人最早在咖啡机旁边用Sun工作站开始编辑阿拉丁系统开始,如何满足一线人员对风险计算的要求,特别是可视化的需求,就一直是阿拉丁优化的主要方向。很多人在开发金融类软件的过程中,对于可视化都没有倾注太多的注意力,然而人在面对过于复杂的一些投资组合的时候,特别是固定收益产品组合那些复杂的结构和条款,变化的利率环境下的关联,是需要更加直观的看到所有可能的情况,以及求助于系统来获得及时、准确的建议的。这一点上阿拉丁无疑是个中翘楚。
阿拉丁的收入大约占贝莱德总收入的5-10%,并不是占比很高的业务,但是阿拉丁是一个活广告,贝莱德总是对外宣称,是阿拉丁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帮助贝莱德在2008年的血雨腥风当中全身而退,是阿拉丁帮助分析和出售了贝莱德手中的MBS等资产。
然而我们都知道,其实是芬克对于如何计算MBS/CMO/CDO们的风险抱有的执念,和为了满足这种执念而形成的方法论、数据库和计算能力,才能够让贝莱德安然度过2008年,并且持续地发展壮大。阿拉丁系统不过是这种执念和能力的物理存在形式罢了。
甚至,贝莱德系统并不只是阿拉丁,还有使用阿拉丁的人。“人在回路”是保证系统不会出现极端风险的前提,越是精密的系统,在遭遇巨变的时候可能越脆弱,这就需要人的模糊判断的介入。
阿拉丁和投资研究管理体系一同把贝莱德20,000个投资组合和数万员工熔铸为一体,使贝莱德不断膨胀的权力得以实现。在广告词中,阿拉丁全知全在,它可以找到数字背后的数字,但是它是“雌雄同体的阴阳神,一半是人类,一半是机器”。阿拉丁可能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cyborg(电子人)。
系统,或者cyborg金融,并不是引入机器替代人,替代人的能力,而是概括、模型化人的能力,使这种能力外延和泛化,处理以前来不及处理,或者处理不够精确,或者因为决策链路的问题不能有效处理的问题。只有把人的能力变成系统的能力,系统才能够真正的运转起来。
阿拉丁太好用了,甚至带来了额外的风险。《经济学人》在2013年12月的文章《巨石与市场》中担心这会导致人人都征询阿拉丁的意见,最终会导致市场失效,因为市场只有在参与者对未来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才起作用。
如果系统是把我们的能力外延和泛化,但是人仍然在回路当中,似乎是避免这样的极端风险的一种合理方式。
二、贝莱德的主要业务,ETF与金融市场的风险
贝莱德是横亘在瑞士市场指数SMI的惊涛骇浪中的一堵黑岩。
——《新苏黎世报》
贝莱德管理规模最大的资产类型是指数基金,ETF构成了贝莱德资产组合约一半的规模。指数基金不仅是一种优秀的投资工具,在20多年来的数次金融市场动荡当中,指数基金证明自己具备超越其成分股的优异流动性,从而为市场的稳定贡献了力量。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指数基金带来的代理人利益冲突问题,以及高流动性背后的不稳定因素。
1. 买方中的卖方
芬克在第一波士顿建立的优势不仅仅是对投资组合风险的执念,还有对投资银行卖方业务的深刻理解。
最好的卖方都知道,好的点子和产品,很多时候都来自于客户。要把产品卖给客户,最好的方式就是卖给客户那些对客户自己定义的需求进行标准化而产生的产品。芬克在第一波士顿创制CMO的经历,使他深刻洞察客户对资产组合的风险和收益的理解能力。投资者们的初衷是追求相对低风险之下的高回报,然而很少有投资者能够坚持这种初心。
此时就需要卖方来解释收益和风险的来源,更进一步就是发明出风险和收益似乎在一开始就锁定了的产品。有的投资者偏好低波动,那么他们会在流动性上有所退让,卖给他们高收益债券的组合,告诉他们在保证低波动的前提下,收益更高,流动性也更好;有的投资者偏好高收益,同样可以接受较差的流动性,那么卖给他们私募股权投资,锁定期内缺乏流动性是对高收益的一种补偿。这些产品的背后,可能都是某一次或者许多次企业杠杆收购。
当一家资产管理公司作为买方,已经把风险和收益分拆匹配,卖给不同的投资者,它就已经替代了卖方的作用,或者说,成为了买方中的卖方。
芬克在贝莱德最重要的创新,就是做买方中的卖方,将卖方的专业知识转化为计算机模型,从而将卖方的优势转化到买方侧。
这样的风险在于,有些时候,特定交易的双方无可避免的存在利益的交集,因为为他们提供融资的可能是同一家资产管理公司,此时避免利益冲突的困难变成了规模,资管公司的规模大到绕开它就无法找到合适的交易对手,此时规模也大到只能让监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贝莱德的支柱性业务可以概况为:
①房地产;
②复杂的债券组合,以及对债券组合的深刻理解带来的央行咨询业务;
③私募股权和杠杠收购,贝莱德是最重要的资金提供方,他们购买了大量的高收益债券;
④ETF,来自收购的巴克莱旗下的安硕,在美国和欧洲市场份额分别为40%和45%。
我们再看一看贝莱德创始时期的重要人物:
①拉里·芬克,创始人;
②罗伯特·卡皮托,大总管;
③技术主管贝尼特·戈卢布,阿拉丁系统主管罗伯·戈德斯坦;
④芭芭拉·诺维克,政府关系主管;
⑤拉尔夫·施洛斯泰因(Ralph Schlosstein),卡特总统经济顾问;
⑥苏珊·瓦格纳(Susan Wagner),来自雷曼兄弟的战略收购专家;
⑦休·弗雷特(Hugh Frater),来自雷曼兄弟的按揭金融领域专家;
⑧查尔斯·哈拉克(Charles Hallac),后来成为贝莱德联席总裁。
早期的贝莱德,主要的工作集中在复杂债券组合以及战略并购,而今天的贝莱德除了杠杆并购中的产品创制的角色之外,还是全球ETF的重要管理人,其中许多的ETF都是出自贝莱德的创意。
贝莱德以135亿美元的代价收购了安硕,并将安硕打造为旗下的ETF投资平台。贝莱德是这样评价安硕的:“ETF结合了传统投资基金和个股的最佳功能”。 安硕的负责人马克·魏德曼(Mark Wiedman)表示,ETF的关键是2点,最低费率和最大的交易商(做市商)网络。2013年,当伯南克暗示可能结束taper的时候,安硕旗下的新兴市场基金一天的交易额达56亿美元,高收益债券ETF成交也超过了10亿美元,这个例子充分证明了贝莱德ETF业务能够向市场提供流动性。2020年3月,当美国资本市场出现剧烈震荡的时候,ETF占据了市场40%的交易量,同时跟踪垃圾债券的ETF – iShires iBoxx[HYG]每天换手168,000次,其基础资产中前五大债券每天平均才25次。
魏德曼把ETF看作可以类比集装箱的创新。当ETF的规模足够大,ETF就不再是跟踪底层资产价格的被动产品,跟踪关系反过来了,投资者真正交易的是ETF,ETF才是真正的市场。
2. ETF也是有风险的
过去20年金融领域唯一有意义的创新就是ATM机;回顾过去40年也许还有一个,那就是指数基金。
——保罗·沃尔克 Paul Volcker
当约翰·博格如先知般在华尔街开创事业的时候,老钱和“波士顿婆罗门”的代表性人物内德·约翰逊三世(他的父亲创立了富达基金管理公司,旗舰基金就是彼得·林奇曾经管理的麦哲伦基金)曾经说,“我无法想象投资者会对平均回报感到满意”,这种充满嘲讽的话语在博格看来司空见惯。
那个时候,同行们把这种叫做指数基金的新兴事物称为“博格的蠢物”(Bogle’s Folly),极少有人想到这竟真的是通灵宝玉。
博格把自己和自己的事业看作是小投资者的代言人,他希望能够为小投资者而战,希望把依赖于工资性收入的普通人都变成长期投资者。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把自己创立的先锋领航集团设计为由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共同享有的公司,这样类似于互助保险公司的组织架构,使约翰·博格的财富主要来自于投资先锋500指数基金的增值。
然而博格的想法无法成为华尔街的主流。
很快同行们就把指数基金推到了交易所上市交易,创造了新的赌具——交易所交易基金——也就是ETF。不到30年的时间,ETF基金的规模就发展到了6万亿美元。当先锋同样发行ETF的时候,博格的选择是退出董事会,他认为ETF会诱使中小投资者投机。
金融产品的风险往往来自于,曾经意义深远,服务于可理解目的的创意被无限延伸和滥用,对风险定价和管理为目的的产品走向了反面。金融机构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在某些理想主义者看来是一种原罪。
而芬克则认为,如果看不到风险,那就是没有风险。也可以说,投资者必须努力做到看清一切风险。华尔街常说T.B.D.,也就是there be dragons,金融市场不可能没有波动,必须要看到dragons潜伏在哪里。
贝莱德进入ETF领域的时候,这种创新产品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了,在金融危机余波未平的时候,公司通过向巴克莱收购安硕染指ETF。收购使贝莱德从一开始就成为ETF市场上不可忽视的大玩家之一,特别是在欧洲市场上。10年之后的2019年,贝莱德的安硕占据着欧洲市场45%的份额,以及美国市场的40%。
安硕宣传的竞争优势的核心是“提供多种类型的投资方案——以极大化超越指数的表现为目标,精准基本面与技术面的主动式管理,以及增加对全球资本市场投资广度为目标,高效率的指数型策略”。安硕提供给指数基金的投资者更加复杂的策略和更广的市场/资产类别覆盖度。
资产类别覆盖是很好理解的。在ETF之前,诸如大宗商品、高收益债券等类型的资产,仅仅向特定的大客户开放,ETF使普通投资者同样可以抵抗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而不仅仅是购买股票;更广的市场也很好理解,投资者可以选择并不熟悉的海外市场的ETF,以很低的研究成本介入那些仅基于宏观理由看好,对个股并不熟悉也不想去深入研究的国家的资本市场。
ETF正在成为传统的策略性投资的一种替代。过去的投资者们积极地在市场上寻找任何投资机会,并且将这种行为成为“策略”研究和投资,正如strategic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投资者事实上是在不断调整自己的战术性配置,经济扩张的时候买入科技股,经济放缓买入消费股,通货膨胀压力巨大则是增加商品配置,某个产业政策调整可能让投资人卖出煤炭买入光伏。自上而下或者自下而上的不断调整策略性的配置,既让投资者可以不断地立于潮头,也可以给人战胜市场的幻觉。
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普通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对过低的市场流动性产生恐惧,以及成熟市场导致战胜市场的难度越来越大,指数基金,包括宽基指数和行业指数,逐渐成为投资者策略性或者战术性的调整投资组合的时候,看好或者看空的动作标的物。投资者很快就不再满足于标普500这样已经成熟的指数,越来越多的指数被创造出来,以满足特定投资者基于特定原因对特定行业或者主题的投资需求。
ETF转变为特定投资策略的附属物。ETF的竞争,也从纯粹的低费率和规模(规模大是低费率的主要助力),转变为发现策略和概况投资机会的能力。
归根结底,ETF管理的仍然是OPM(别人的钱,other peoples money),既然是其他人的钱,那么如何让其他的人关注并且赞同这种策略就是关键点,执行效率、跟踪误差都是技术细节。
2014年5月,美联储理事杰里米·斯坦(Jeremy Stein)说,影子银行的本质可能就是赋予人们对非流动资产的流动性权利。在流动性不高的部分成熟市场,ETF也扮演着类似的角色,没有创造指数的人的努力,就不会有一个系列的股票被概括成一个主题,变成一支ETF而获得买入和流动性。
随着债券ETF规模的不断扩大,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债券市场,那里流动性更低,ETF与影子银行的相似性也更大。“我们对银行毫不留情的压制意味着我们的金融体系越来越多地与银行脱钩,从可见的、受监管的部分,转变为看不见、不受控制的存在。” 银行行业分析师理查德·波夫(Richard Bove)如是说,他认为美国不平衡的贸易导致了美元过量发行,最终泛滥的美元在金融衍生品那里找到了出口,CDO、CMO、CDS最终形成了风险。
那么,ETF又在制造什么样的风险呢?
一种显而易见的风险,在霍华德·马克斯2015年的备忘录当中有非常好的描述:“只有一匹马的比赛似乎很符合要求。赌徒赌上所有的钱,但是在比赛中途这匹赛马突然挣脱束缚,跃过篱笆,疾驰而去。”当ETF创造的流动性成为了市场上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流动性,当ETF被投资者当作主要的标的而不再关心底层资产,风险就会无可避免的积聚起来。
同样是在2015年,在CNBC的现场访谈当中,孤狼伊坎直接向桌边的芬克开炮,说贝莱德就像在悬崖上开着一辆满载毫无防备的投资者的大巴车,直到撞上一堵黑墙。他针对的是债券领域的风险。在低利率环境下,对债券的专业知识了解不多,或是缺乏固定收益分析技能的投资人通过ETF投资于企业信贷,而巨额信贷资金也没有用于企业发展,就连以工程师文化为图腾的波音也不是用钱来做研发,而是回购股票推高股价。
ETF在资产端流动性的独大趋势,和负债端投资者对底层资产的认知缺失,是ETF未来最重要的风险,ETF对资本市场的意义,特别是在信贷领域逐渐取代影子银行的地位,也是公众和监管必须关注的趋势。
3. 贝莱德曾经的错误投资和涉及的丑闻
贝莱德从来不是华尔街典型的公司,这一点从贝莱德员工极少涉及华尔街交易员那样的花边新闻就可以看出来。不过书中也列出了贝莱德的一些失误和涉及的丑闻。
①纽约史蒂文森镇地产项目:
史蒂文森镇是纽约的大众公寓项目,最早由大都会人寿与二战后开始建设,申请成功的教师、警察等普通人,可以在自己的阳台上欣赏到纽约的天际线和帝国大厦的美景。史蒂城在半个世纪当中都是25,000名居民喜爱的社区,由于有“现状保护”权利,即便市面上类似社区的租金价格上涨到数千美金,居民仍然继续支付数百美元的固定租金。
史蒂城项目在21世纪初由大都会人寿以54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贝莱德和铁狮门的联合体。铁狮门提出了上调租金的计划,房客反击并诉诸法庭,房客质疑通过贝莱德投资于史蒂城的养老金类机构投资者,说领取养老金的纽约居民,与购买该项目的养老金投资者代表的加州居民,本来不应该是对立的关系。
最终是房客打赢了官司。
2010年,项目被移交给贷款人,参与杠杆收购的股权投资人亏掉了本金,这其中就包括贝莱德代理的加州公务员退休基金和加州教师退休基金。2015年,史蒂城项目出售给了黑石集团,价格是53亿美元。
②雷曼兄弟:
2008年上半年,风雨飘摇的雷曼兄弟股价跌掉了60%,6月份的报道中,卡皮托还表示对管理团队的信心,彭博社报道称贝莱德购买了雷曼兄弟的股票。贝莱德的风险管理保护了公司和投资组合,但是贝莱德管理层也没有抵抗住抄底的诱惑。
9月13日,雷曼的股价较07年高点已经跌去95%,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和财政部正在曼哈顿闭门讨论雷曼和美林的命运,当天晚上芬克准备坐飞机去新加坡,上飞机前他打电话给参加会议的代表问道:“我能飞吗?”当时看起来美国银行对雷曼的收购有了眉目,得到肯定答案的芬克上了飞机。
16个小时之后,走下飞机的芬克第一时间就发现,雷曼兄弟破产了,当时是贝莱德最大股东的美林被卖给了美国银行。他后来对记者说,那一刻就好像老版《人猿星球》当中男主角在自以为的外星球上发行了自由女神的遗迹,突然发现地球文明已经毁灭了一样。
③Cum-Ex税务欺诈丑闻:
“Cum-Ex”指的是在分红当天,对股票进行出售和再次买入的操作,交易时间接近导致的漏洞,使监管和税务机构无法判定股票产权属于买方还是卖方,因此买卖双方都可以从税务局拿到资本利得税的退税。在德国资本市场上,分红前可以用先卖空股票,在分红后再购回,形成多次易手。
早在2012年德国税务机构就在尝试修补漏洞,但是金融业的创新行为总是在寻找新法规的漏洞。据估计,Cum-Ex导致多个欧洲国家损失了超过550亿欧元的税收,其中德国政府损失超过300亿欧元。
2018年,因为可能向欺诈丑闻的主角借出股票,贝莱德在慕尼黑的办公场所遭到警方搜查。至今公众都并不清楚贝莱德在这桩持续多年的税务丑闻当中真正的角色,不知道借出股票的时候贝莱德对股票的用途是否知情。
不过除了少数像Cum-Ex这样责任模糊的丑闻之外,贝莱德在监管看来比传统投行守规矩的多。部分原因是因为芬克经常强调,资产管理公司只是投资者的中介,“这不是我的钱”,这就意味着资产管理公司既不会用资本金去冒险,也不会像银行一样使用由政府担保(通过储蓄保险)的钱去冒险。另一个原因则是贝莱德总是小心地维持自己不被监管注意,游离于主流视野之外,避免成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SIFI, Systemically Importa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三、新时代的资本主义与资产管理公司
社会要求公司为社会目的服务。
——拉里·芬克,公司投资者的首席仆人,他喜欢说,“我们的客户是消防员和老师”。
ETF的成本优势导致其终极竞争对手是交易所,而这种成本优势的建立是因为流动性,投资者更多的交易ETF,以及ETF代表的特定类型的投资策略,和投资者更加看重投资标的的回报属性,看轻投票权是有关系的。
贝莱德的地位也使其暗池成为全球资本市场最大的暗池,也就成为了一种私人交易所,并且是世界上最大的交易场所之一。贝莱德借以推动整个金融市场变革的工具是ETF、影子银行,以及私人交易所和暗池。
1. 公司职责的转变
公司只有一项社会责任,即利用其资源增加利润。
——弗里德曼,约1970年。
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理论是弗里德曼等人在1968年前后提出的,可以看作是当时风起云涌的左翼运动的对位。
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理论根基是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认为公司只需要关心经营,为股东创造价值,用户、员工和相应的社会责任在自由市场的安排之下都能各归其位。
然而对股东价值最大化过于原教旨的信仰会导致大量的问题,比如劳资矛盾和社会责任的缺失,从福特汽车到好时巧克力(KISSES),福特和赫尔希都致力于员工福利,但是到头来员工还是需要组织起来,选出自己的代表。通用汽车在2009年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破产重整规模最大的制造业企业,公司与UAW(美国汽车工人工会)的恩怨情仇是公司破产的重要原因。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总是在不知不觉之间走向与员工的对立。
股东们要想日子过得好,就不能不考虑这些问题。
1894年普尔曼皇家汽车公司(生产豪华卧铺车厢)大罢工,涉及26个州24万工人,政府派军队镇压,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代劳资矛盾的高峰。2007年通用汽车大罢工,则是美国自1976年以来因劳资谈判而引发的首次全国性罢工,2019年,作为新通用汽车最大股东之一的UAW再次组织了4.6万名工人罢工。
从J.P.摩根开始,金融资本主义逐步掌控世界,他们主要依靠的是借助金融手段染指的工业集团,包括美国钢铁、通用电气、AT&T、西屋电气和波特兰水泥。美国企业分散持股和直接融资的传统始于一战期间战争公债对投资者的教育,因此金融寡头和银行融资得以隐于幕后。
由于监管的原因,到60年代金融资本主义在美国和欧洲的影响力有所减弱,股东价值最大化理论的提出,给金融资本主义新的生命力。投资者通过董事会,更多的介入公司管理和价值分配。这种价值分配,有可能激化劳资矛盾等企业固有的内部冲突。
许多人会觉得,董事会代表股东利益天经地义。确实,英美企业的董事会代表股东的利益,但是德国法律要求略等于董事会的监事会作为企业内部机构,平等对待股东、员工等各方力量。
因为员工不仅仅是员工。
20世纪70年代,1/10的美国人为25家最大的美国公司工作,他们既是员工,也是最典型的消费者,他们是“典型的美国人”。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当年福特工会的头头去参观机器人工厂,机器人研发的人很骄傲的对工会的头头说,以后汽车工人都没有用了,没人会雇佣他们造汽车,工会头目说:“是的先生们,但是有个问题,机器人并不会买汽车,造了汽车卖给谁呢?”
而德国的莱茵兰资本主义是这样的:管理层和监事会成员结成利益共同体,彼此熟识,定期会面;企业与主银行深度绑定,银行持股企业、深入参与公司管理,并且在贷款上有决定权;监事会在做决定的时候,必须考虑员工等股东之外的利益主体,并加以平等对待。明镜周刊称这种“基于共识和共同决定的制度”,德国公司得以对抗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
德国式的资本主义,曾经代表了与英美资本主义截然不同的另外一条道路,北欧诞生的第三条道路,也受到了这种欧洲大陆思想的影响。
然而指数基金的持续扩张,正在使欧洲人屈服于美国的资产管理公司和美国的资本主义模式,特别是金融资本主义重新扩张的控制力。
2. 指数基金对金融资本主义的推波助澜
大公司的权力被打破,金融资本家的统治再次降临,资产管理人代替银行家掌控金融体系,形成了金融资本2.0。
——杰拉尔德·戴维斯 Gerald Davis,《贝莱德如何成为新J.P.摩根》,2012
普华永道2014年发布了一份报告,题目是《美丽新世界》,这篇报告研究了资产管理行业,预测2020年资产管理公司将从银行和保险公司的阴影中走出,大放异彩。他们提出,银行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是金融创新的引领者,从政治家到普通人都沿着他们设定的轨道前进,但是金融危机摧毁了对银行的信任。普华永道预测,2020年资产管理公司将管理145万亿美元(2014年为74万亿美元),到2050年会增长到400万亿美元。
随之而来的是投票权。
许多股东事实上并不想要投票权。股东们把投票权以AB股的方式让渡给创始人和管理层,也有很多股东,包括一部分机构股东,把二级市场上持有的投票权交给股东代理机构。规模最大的股东代理顾问是机构股东服务公司(ISS)代理750万张选票,超过4万亿股的表决权,第二名是加拿大养老金的子公司格拉斯-刘易斯。
而更多的投票权掌握在资产管理公司手中。
我们生活在资产管理公司的时代——安德鲁·霍尔丹(Andrew Haldane)在2014年这样公开表态,他是英格兰银行金融稳定部负责人。霍尔丹指出储蓄者正在成为资产管理公司的客户。
人类预期寿命的增长,经济和财富的增长赋予资产管理公司极大的权力,资产管理公司既不会用自己的资本冒险,也不会使用受政府担保储蓄资金去投资,但是规模构成了风险。受到冲击的AMC会抛售债券和股票。霍尔丹说,我们对银行的行为和破产风险的研究已经有几个世纪之久,而对大型资产管理公司的研究才刚刚开始。
超级资产管理公司如贝莱德,和银行、投资银行一样开始面对日益增长的不信任。基金经理应当是解决方案,而不是问题的一部分。
随着指数基金规模的日益增长,以及越来越多的成熟市场上市公司,创始大股东的股权已经非常分散,持股数量居前的都是资产管理公司,特别是他们的ETF基金。
指数基金三巨头:贝莱德、先锋领航、道富,持有了美国主要的企业13%的股份 其持有苹果的股份由2009年的9%上升到2020年的17%。也许10年之后这三家公司会持有美国主要公司1/4的股份。
3. 指数基金和资产管理公司必须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如果你俯瞰街道,望一眼陶努斯安拉格(法兰克福金融区的一条街道),那么你只会看到人渺小如蝼蚁。那里是世界,正常的世界,但我们不属于那个世界……我们在摩天大楼的顶部办公,我们看着窗外,心里想,我们是最聪明的,我们是天才,你们都是蠢货。
——汉诺·伯杰(Hanno Berger,德国税务律师,Cum-Ex欺诈案参与者)的助手
当私募股权投资开始介入并且掌控企业的时候,PE基金们把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理念转变为所有者获利,结合了华尔街收缩资产负债表的方法和咨询公司对全流程成本压榨的方式,至于创造还是毁灭就业,他们毫不关心。工作向低劳动力成本外包的趋势无法继续时,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就会顶上。
贝莱德不仅大量投资于私募股权投资,更是杠杆并购不可或缺的的债权投资人。没有贝莱德介入的私募股权市场是不可想象的。
在全世界的很多公司,贝莱德不仅仅是最大的股东,经常非公开的干预公司管理,不达目的不惜以反对票表明态度(交流干预的频率大约是参加股东大会投票的1/10);贝莱德还是公司主要的债权人,既提供贷款也负责安排债券交易,没有贝莱德的网络和安排,公司就无法在固定收益市场上拿到钱。
对私募股权投资的道德诘难是容易的,毕竟他们是在为了增加运营效率裁员,而且在几年之内就会拿走数十亿美元的利润。而ETF被诘难的地方在于被动投资并不能实现将资本引导到最富有生产力、创造最多就业机会和普遍提高生活水平的地方。ETF的投资者和管理人也许会辩解,赚取利润是一切责任的前提,甚至是责任本身,但是当ETF的被动投资的规模大到目空一切,责任不可能不如影随形。
贝莱德既有股权也有债权,更重要的是它有数据,而且还有对世界各国监管机构、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影响力。贝莱德就像巨型乌贼,活在黑暗的深海,活在传说里,巨大而致命。贝莱德作为有责任的投资人仍然面临尴尬,它并不能代表整个社会,它只代表拥有金融资产的阶层,然而它却借助持股的成千上万家企业对全社会施加影响。
贝莱德也带来了隐秘的风险,因为阿拉丁系统和贝莱德的使命是规避风险,事实上它在阻止变革。系统记录和比较行为,任何偶然或有意为之的改变都被识别出来,过去的轨道不可漂移,过去的世界不可忘却,结果就是变革消失了。
贝莱德正在成为为金融界树立规则和设定节奏的机构。贝莱德的崛起是一个符号,是社会分裂的象征,储备和兜底的责任转到个人身上,人们必须为失业、疾病和养老做好准备,否则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每个人都在为自己而战。
并不是贝莱德带来了风险或者承担了风险管理的责任,而是我们的社会把每个人独立出来,拿走了社会本应笼罩他们的保护伞,把风险留给我们每个人去管理,此刻,我们不得不把管理风险这件事交给最专业的人。目前看来,许许多多的人选择了贝莱德来管理自己的风险,因此,贝莱德就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
附录:
《金融帝国贝莱德》
作者: 【德】海克·布赫特
译者:石建辉
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23-3
页数: 320
定价: 118.00元
ISBN: 9787300310237